阿布扎比的夜空从未如此沉重,亚斯码头赛道被探照灯切割成明暗交错的战场,每一盏灯都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维修区尽头,红牛车队的无线电突然传来工程师压低的声音:“维斯塔潘进站了,”梅赛德斯指挥墙上,所有人的目光投向赛道显示器——第53圈,比赛还剩最后五圈,汉密尔顿领先1.2秒,但维斯塔潘换上了全新的软胎。
“凯恩。”车队的呼唤通过耳机传来,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,“你怎么选?”
凯恩·罗森伯格盯着前方汉密尔顿赛车的尾灯,那盏红灯在直道尽头收缩成一颗遥远的星辰,他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击,大脑在千分之一秒内完成了运算:进站换胎,可能失去位置;留在场上,用这套跑了28圈的硬胎面对维斯塔潘的新软胎,无异于自杀。
“我留在外面。”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。
工程师沉默了两秒。“凯恩,轮胎数据已经到极限了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凯恩说,“所以我必须让它们超越极限。”
这不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在临界点做选择,十年前,当他还是一名卡丁车手时,就在暴雨中的决赛圈选择了不换雨胎,用光头胎在逐渐变干的赛道上跳了一曲死亡之舞,最终以领先第二名半圈的优势夺冠,那次胜利让他获得了第一份F1青训合同,也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:当所有人都向右转时,向左转的人要么撞墙,要么发现新大陆。
第54圈,维斯塔潘追到了DRS区内,红牛赛车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,在直道上不断逼近,凯恩的赛车在高速弯中有些挣扎,轮胎已经失去了抓地力峰值,每一次转向都伴随着轻微的滑动,但他没有松油门,反而将油门踩得更深——在F1的世界里,后退一步就是悬崖。
“维斯塔潘在5号弯尝试超越!”解说员的声音几乎撕裂,“凯恩守住了内线!天哪,他们的轮毂几乎擦碰!”
两辆赛车并排冲进6号弯,刹车点的选择成为生死判官,凯恩比平常晚了5米刹车,赛车在入弯时剧烈摆动,但他奇迹般地控制住了,出弯时,他抢回了领先位置。
观众席爆发出海啸般的惊呼,梅赛德斯的工程师们紧紧抓住围栏,指节发白,凯恩的父亲——一位退休的拉力赛车手——在看台上闭上了眼睛,他太熟悉这种游走于失控边缘的感觉,二十年前,他在芬兰冰雪森林的某个弯道做过同样的事,只是那次,他撞毁了三棵松树。

最后一圈,维斯塔潘显然已经不耐烦了,他在每一个弯道都发起攻击,但每一次,凯恩都像预知了未来般封堵了线路,这不是防守,这是一场精密的心理博弈:凯恩知道维斯塔潘会在哪里进攻,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是对手,会在哪里进攻。
“还有两个弯道!凯恩领先0.3秒!维斯塔潘在直道上拉近距离,他能做到吗?”
最后一个弯道,维斯塔潘选择了非常规线路,试图从外侧超车,这是孤注一掷的赌博,如果成功,将成为F1历史上最伟大的超车之一;如果失败,他可能会冲进缓冲区,甚至撞墙。
凯恩从后视镜里看到了这一切,他的大脑再次高速运转:如果防守内线,维斯塔潘可能会从外侧抢走出弯速度;如果防守外侧,内线就会敞开,时间不允许他犹豫。
他选择了第三条路。

凯恩轻轻向外侧移动了半米,既不完全封堵外侧,也不完全敞开内线,这个微小的调整改变了整个弯道的几何学,维斯塔潘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:继续走外侧,出弯角度太差;切回内侧,距离又不够,就在这一瞬间的犹豫中,凯恩已经全油门出弯。
冲线。
098秒的差距。
梅赛德斯车库爆炸了,人们拥抱、尖叫、哭泣,凯恩慢慢将车开回维修区,摘下头盔时,他的脸上没有狂喜,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平静,记者们涌上来,将麦克风塞到他面前。
“凯恩!最后一弯你是怎么想的?为什么选择那样的线路?” 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,说:“我只是没有选择他们期待的选择。”
这句话后来被印在了梅赛德斯工厂的墙上,凯恩的胜利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冠军,它是一个宣言:在速度和战争的临界点上,唯一的规则就是打破所有预设的规则。
那天深夜,当香槟的泡沫终于散去,凯恩独自一人回到了赛道上,亚斯码头已经空无一人,只有维修区的几盏灯还亮着,他走到最后一个弯道,站在自己刹车的地方。
地面上还留着轮胎的橡胶痕迹,四道黑线交织在一起,像某种神秘的符咒,他蹲下来,用手指轻轻触摸那些痕迹,冰冷,粗糙,真实。
二十年前,他的父亲在撞毁赛车后对他说:“速度不是关于你敢踩多深的油门,而是关于你敢在最后一刻相信什么。”那时他不懂,现在他明白了,在战争与速度的临界点上,你要相信的不是赛车,不是轮胎,甚至不是自己的技术,你要相信的是,当整个世界都在告诉你必须松开油门的时刻,你还能再踩下去一毫米。
凯恩站起身,望向赛道的尽头,那里,黑暗与光明相互吞噬,就像每个车手职业生涯中必须面对的临界点,他知道,今天他跨过了那个点,但明天,又会有一个新的点等待着他。
唯一不变的是,他永远不会在关键回合手软。
就像父亲说的那样:有些人天生就知道刹车点在哪里,而另一些人,他们天生就知道,有些弯道根本不需要刹车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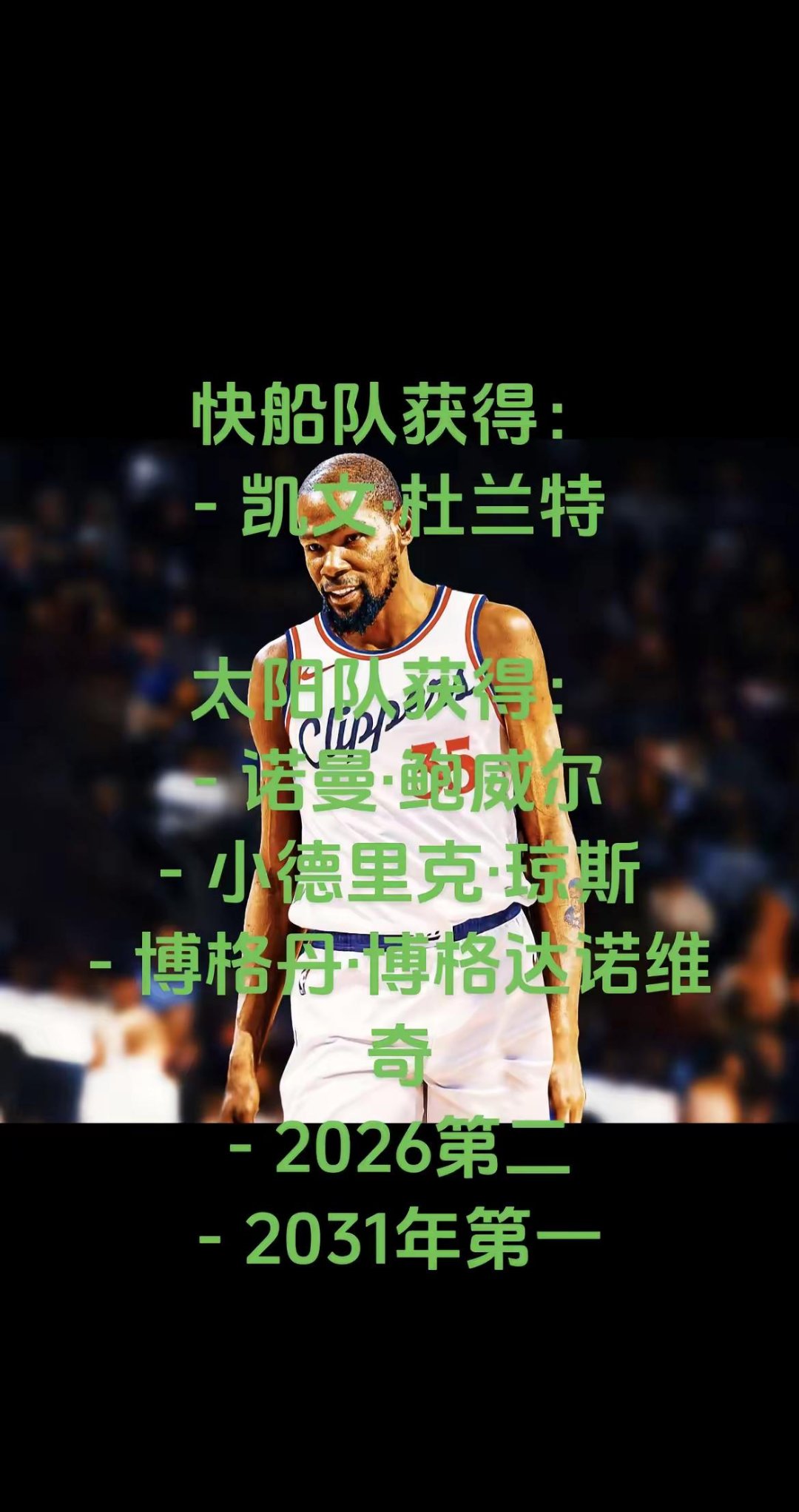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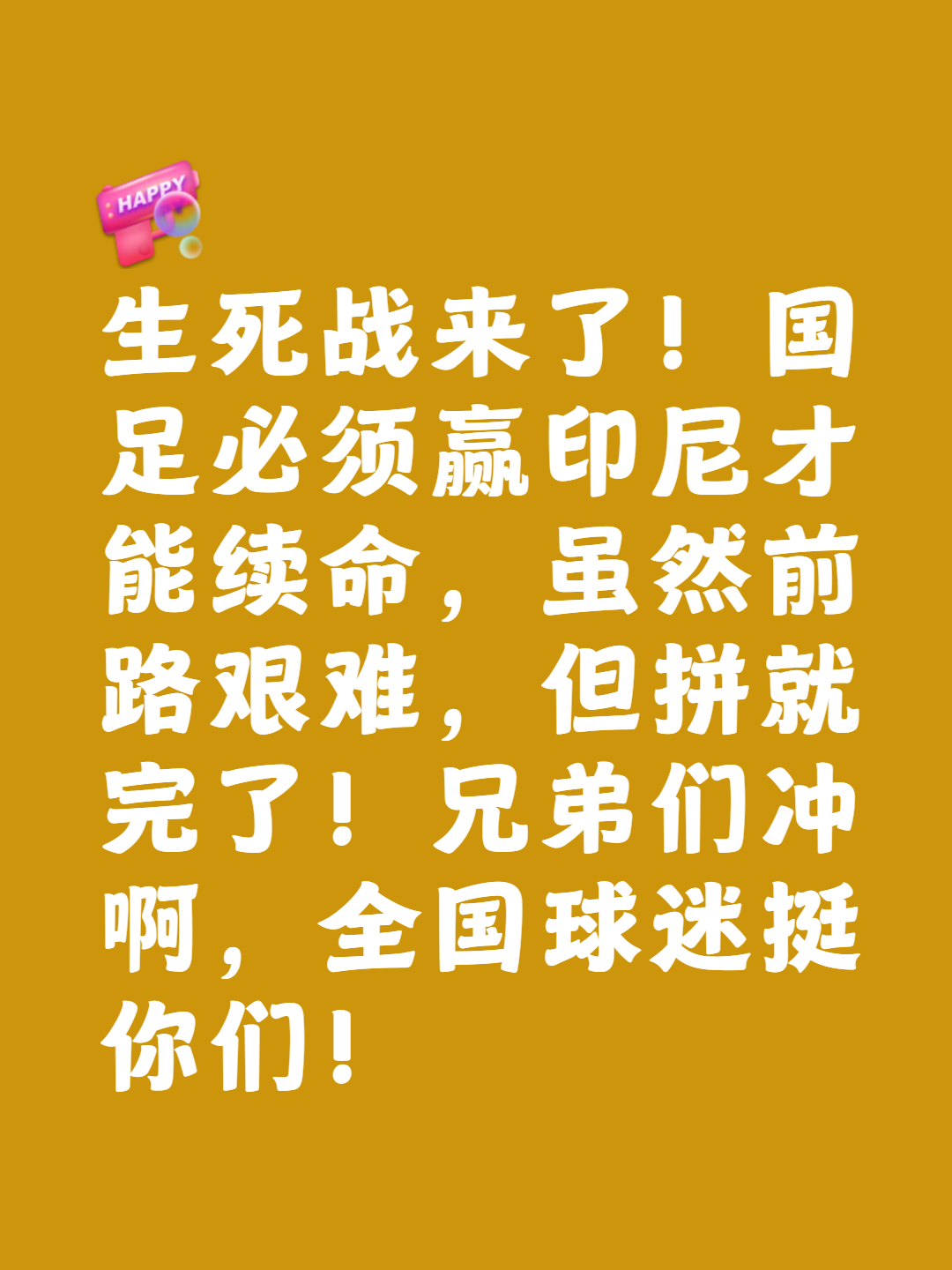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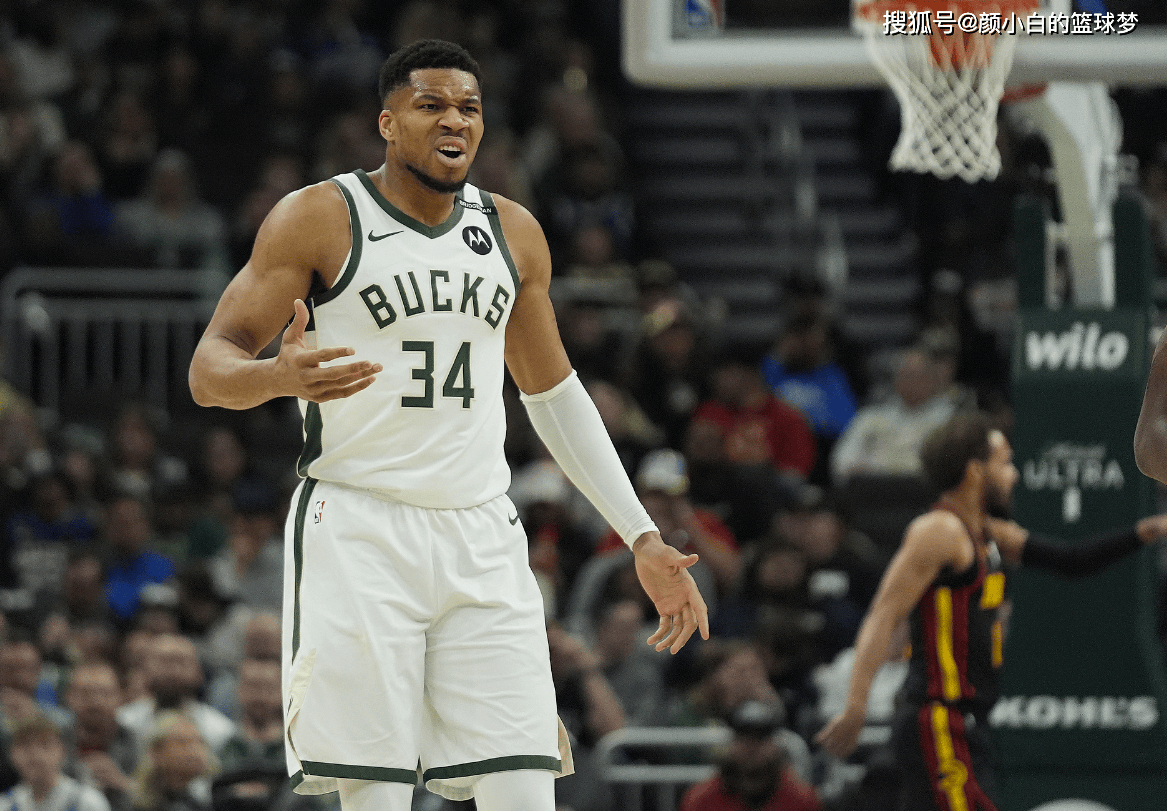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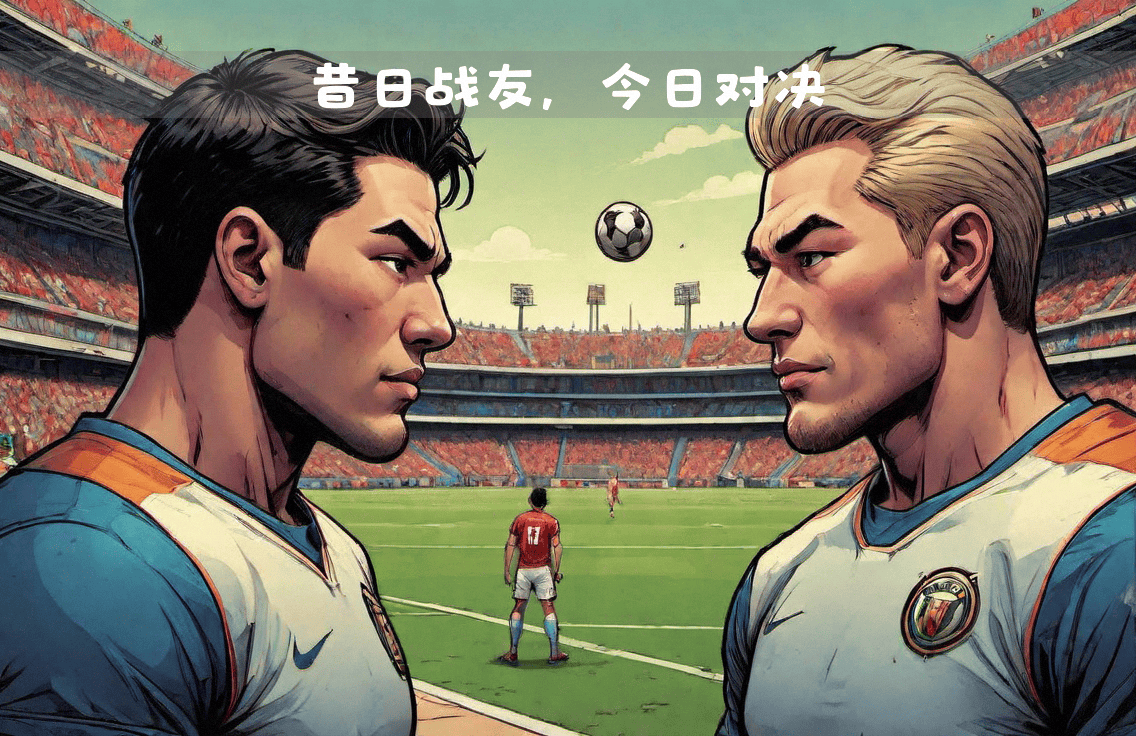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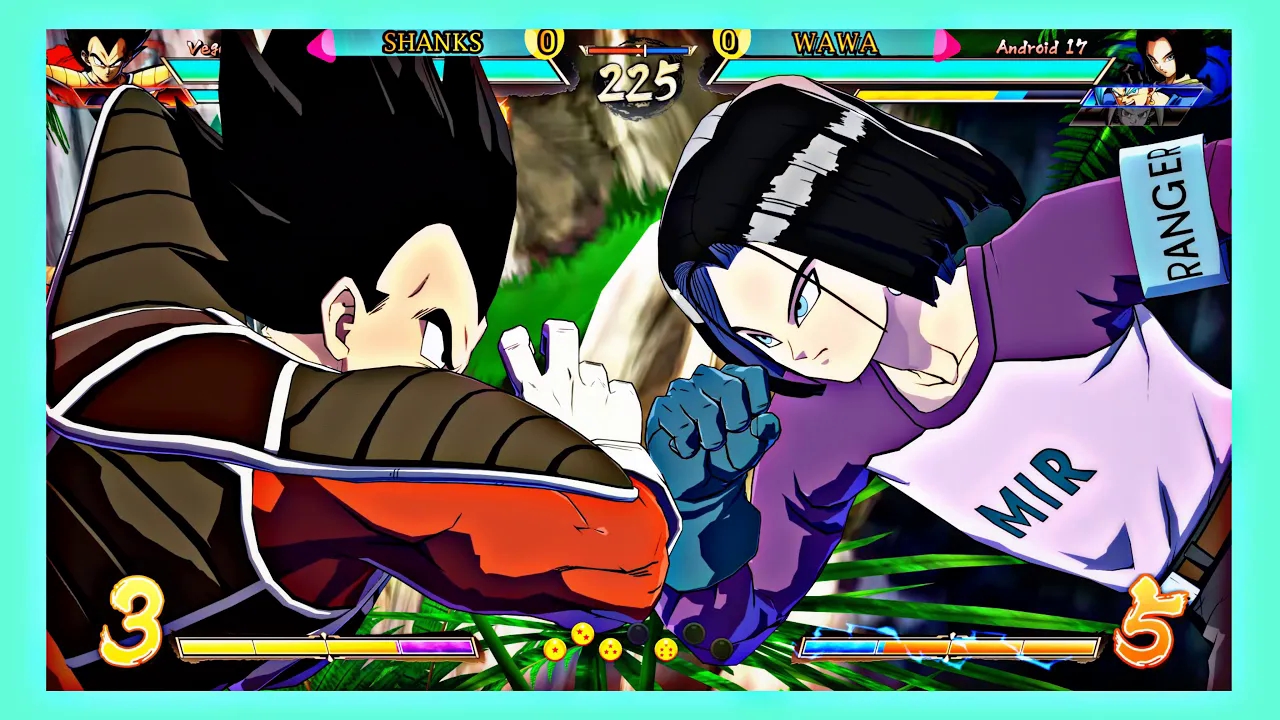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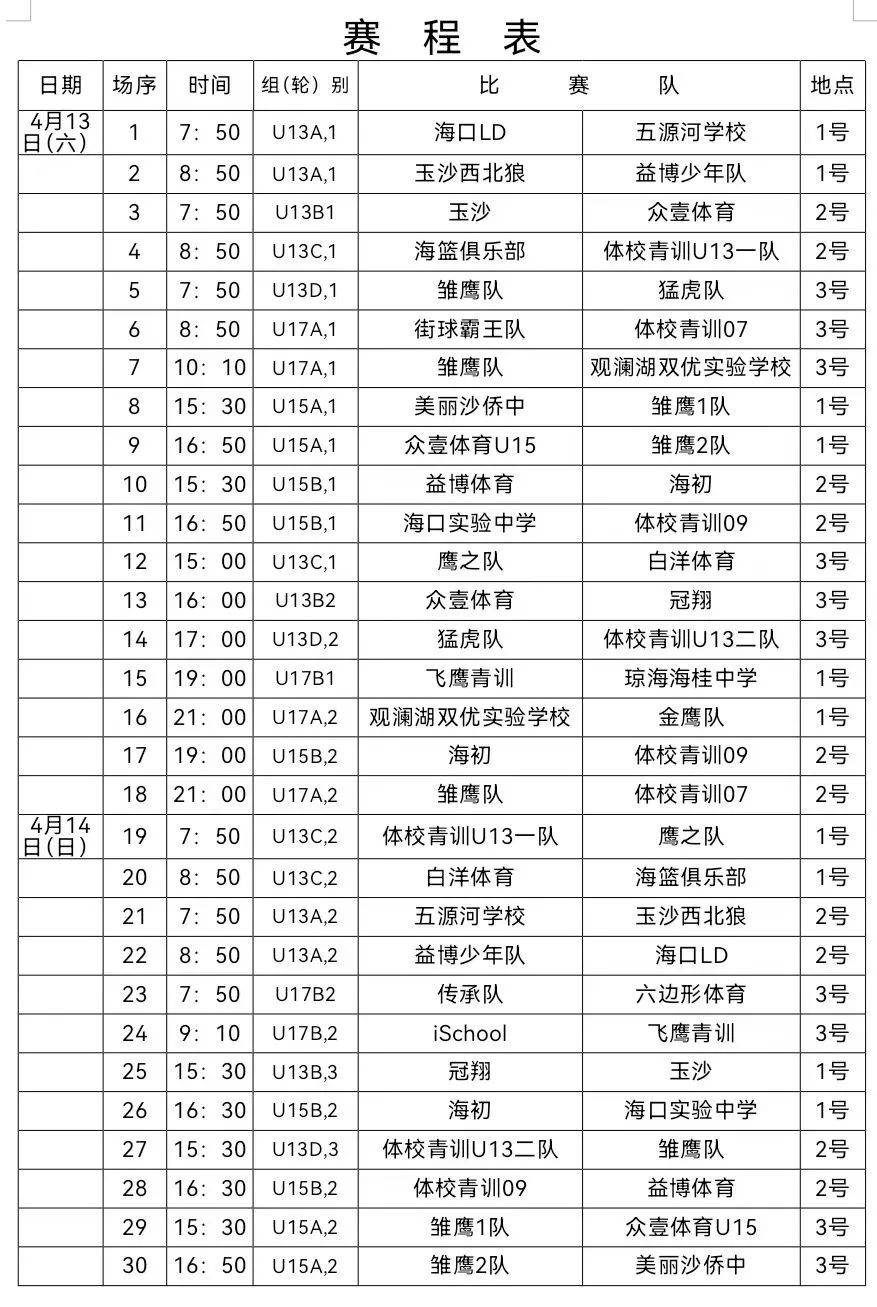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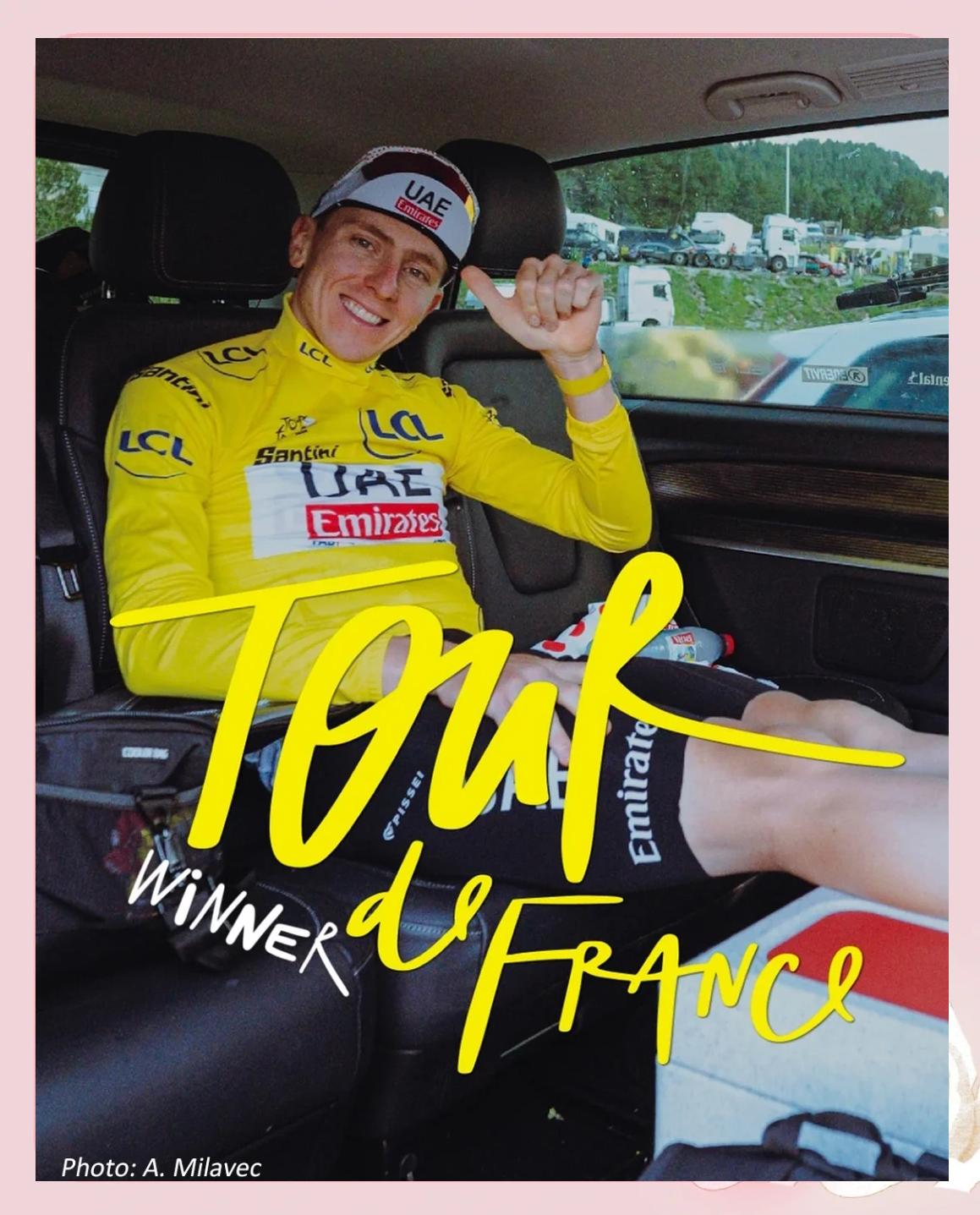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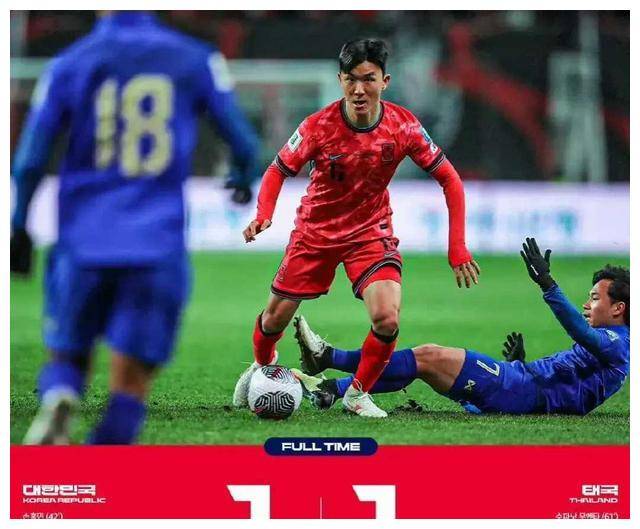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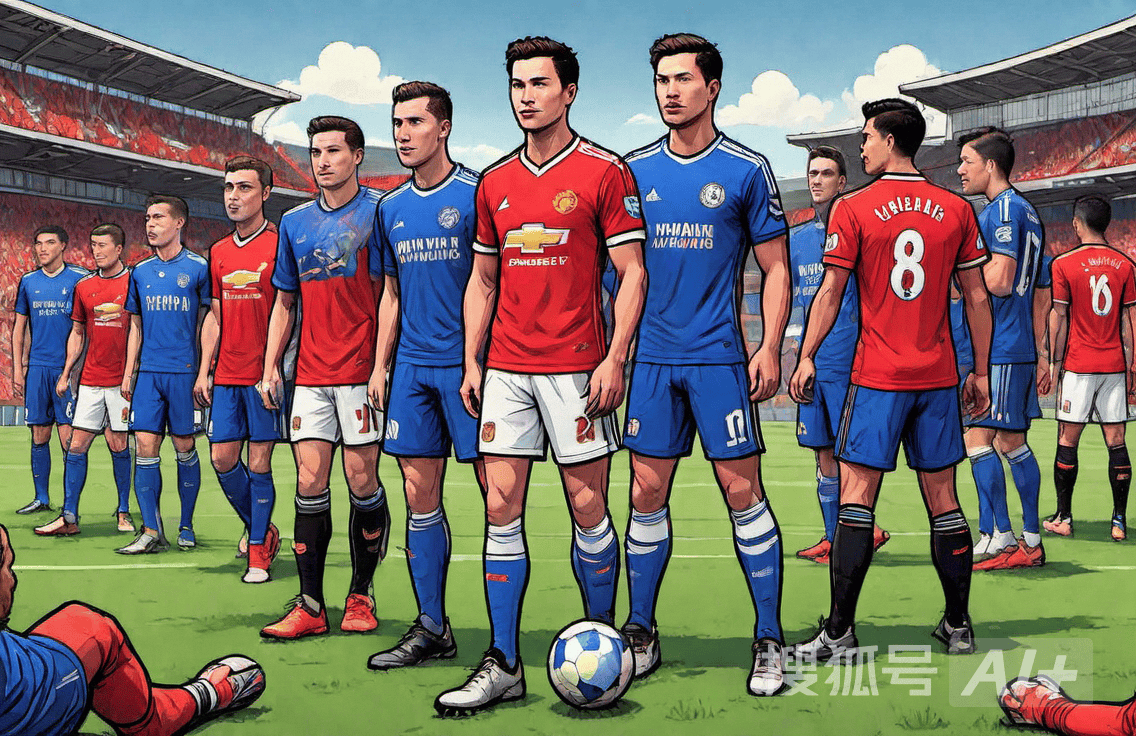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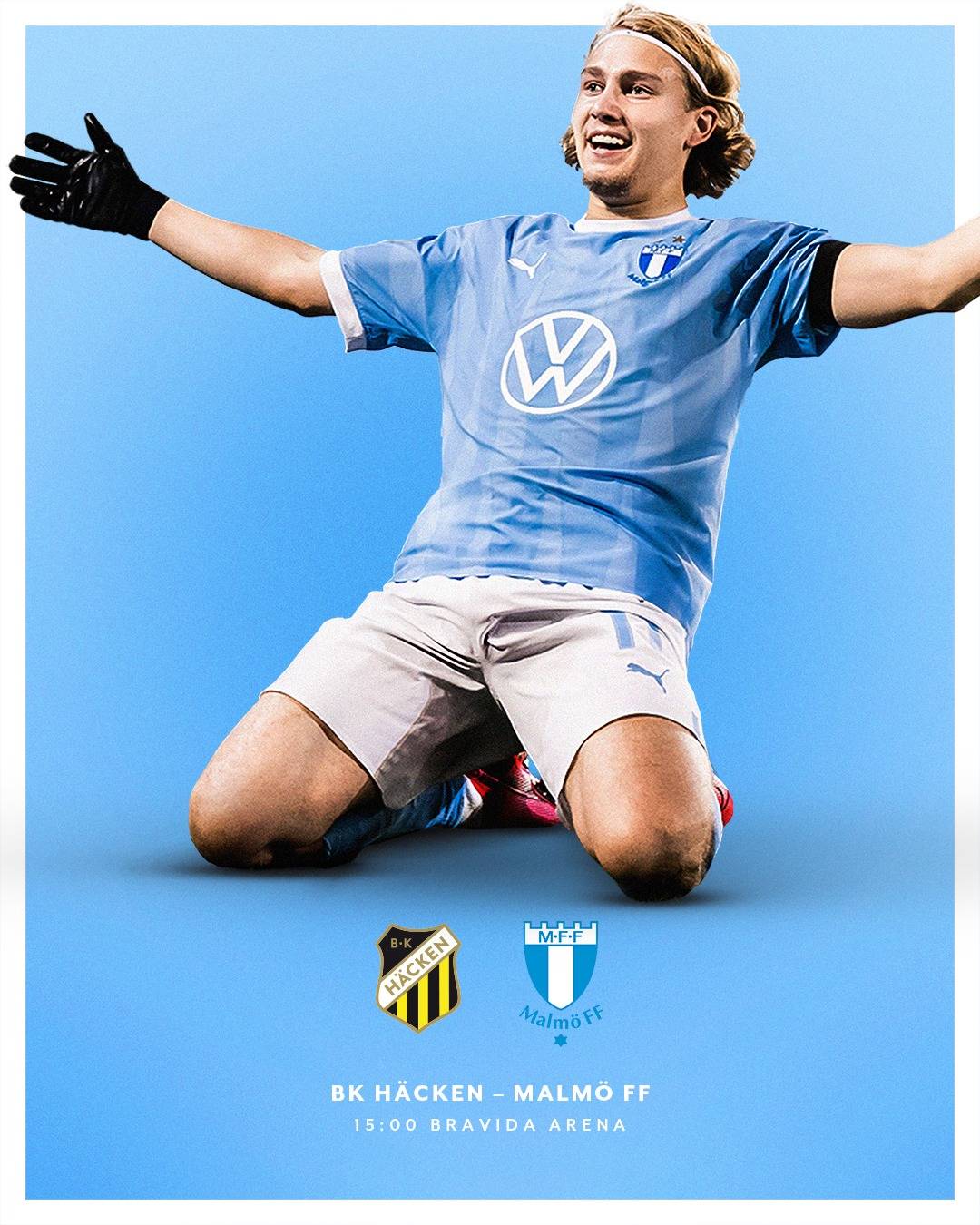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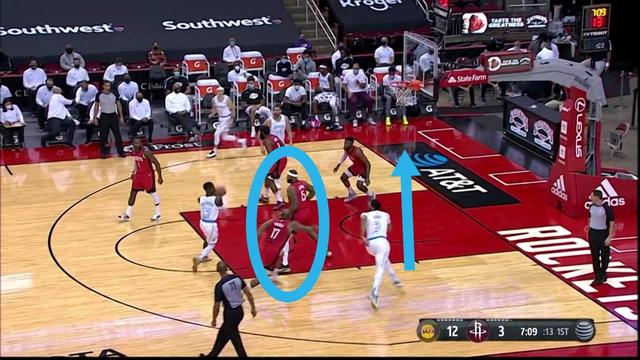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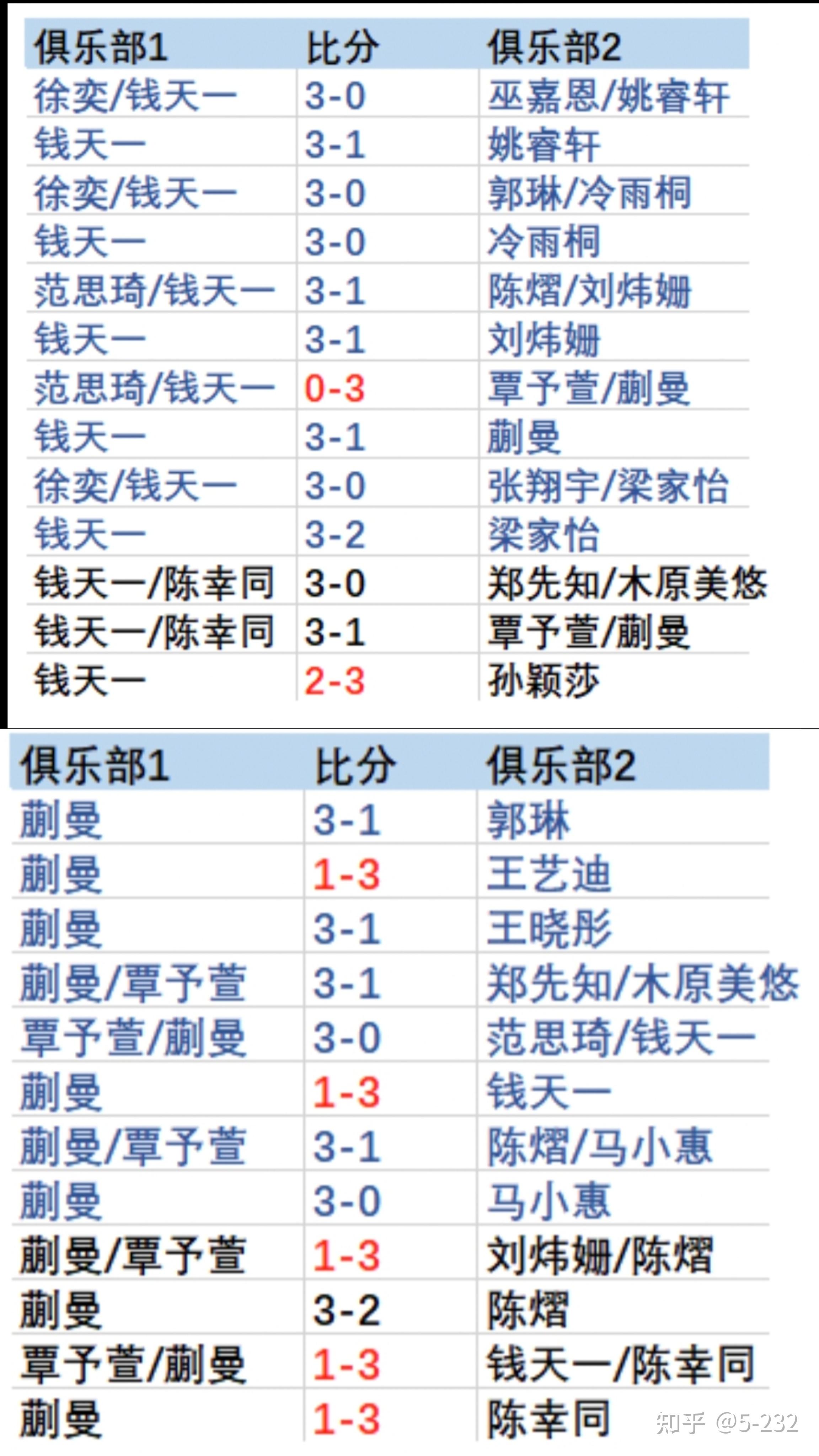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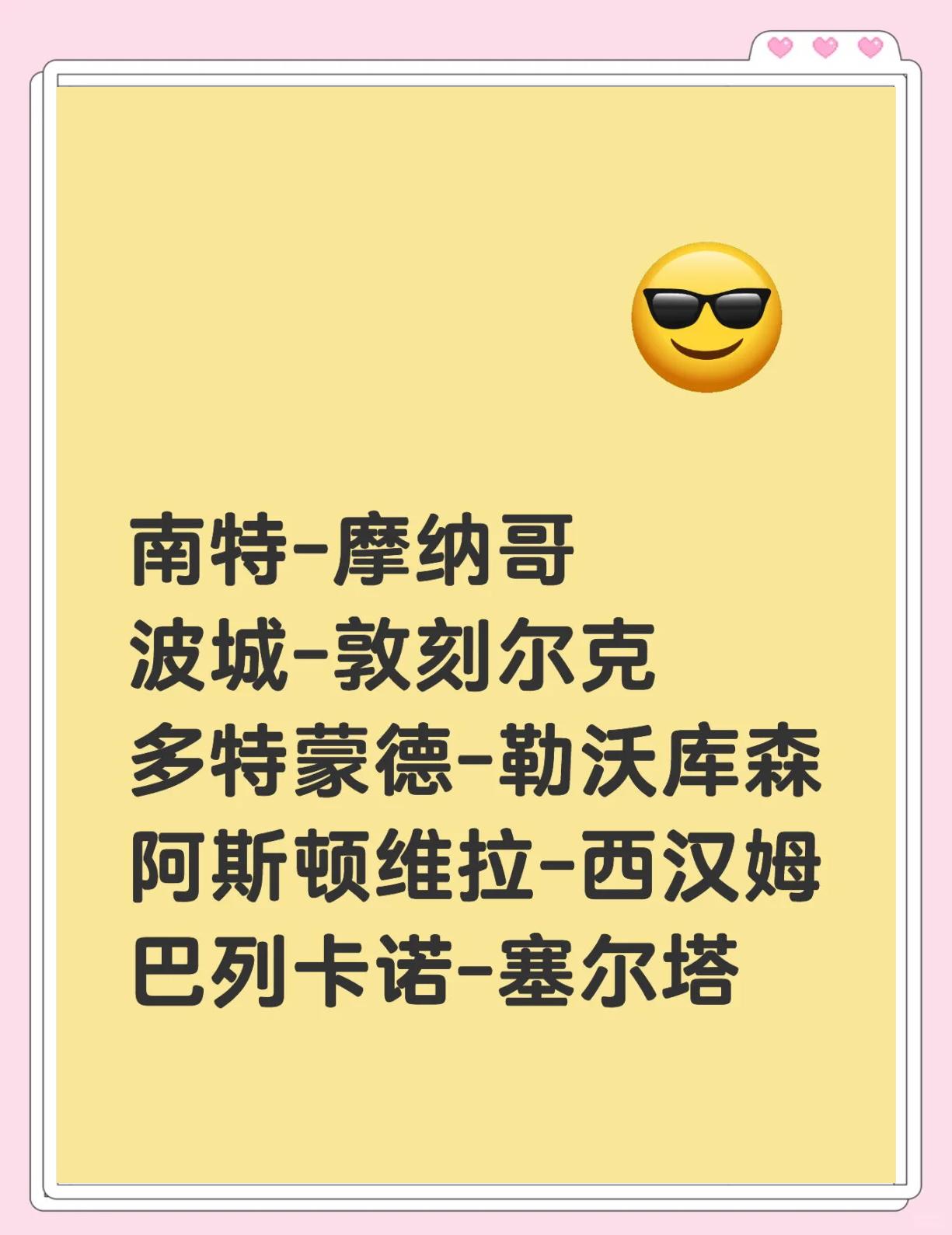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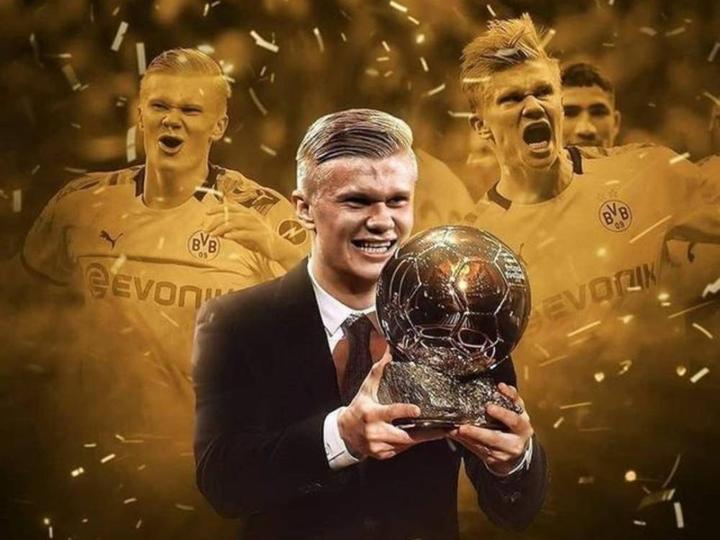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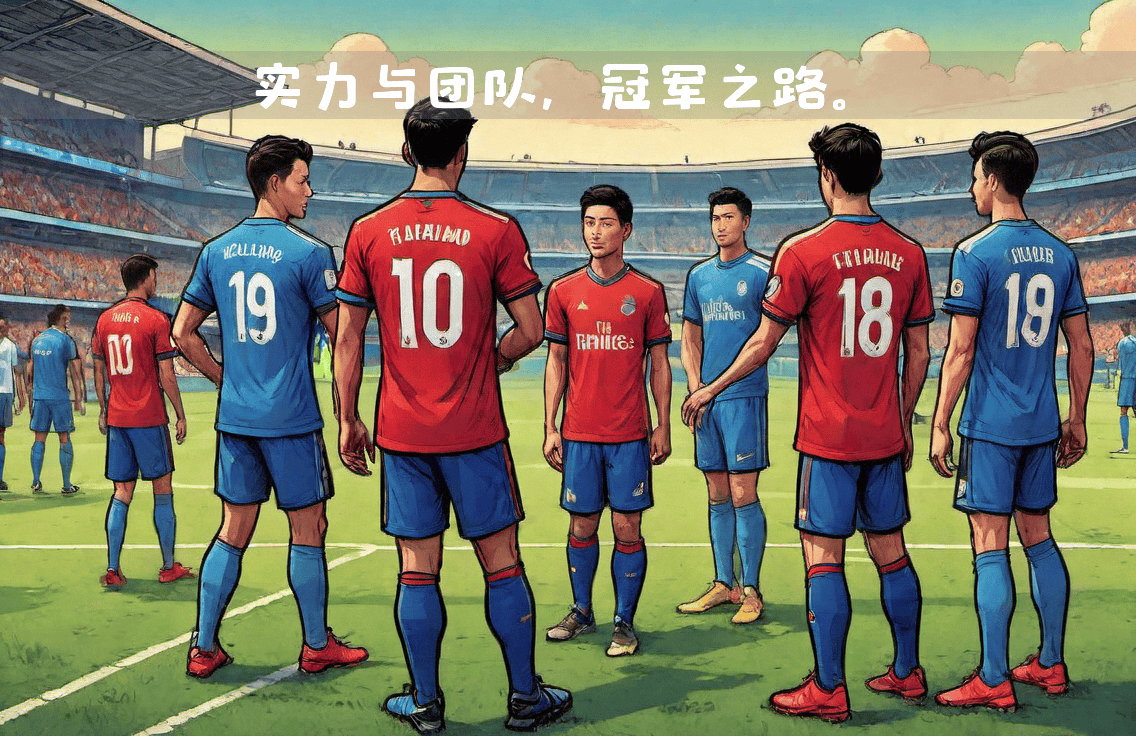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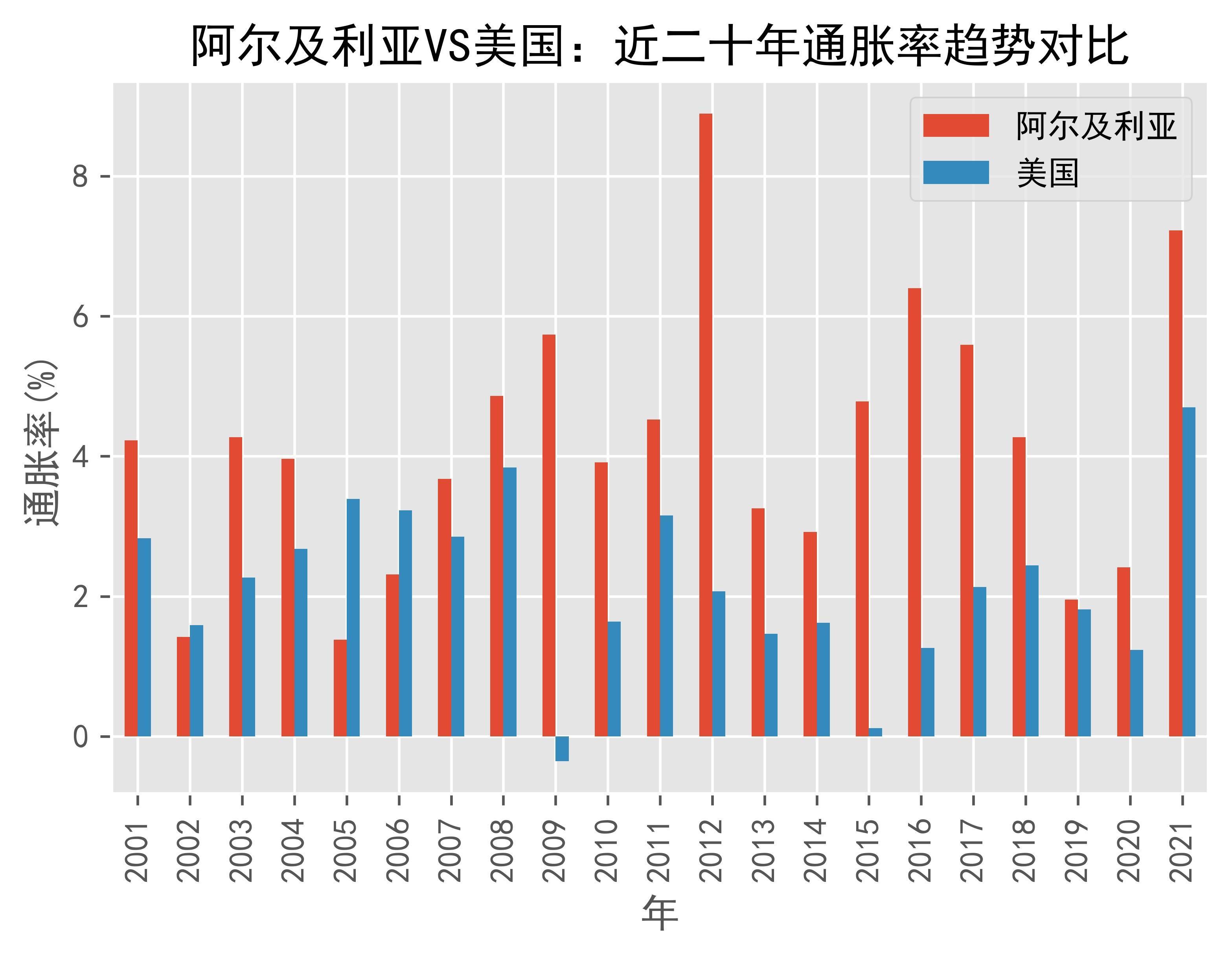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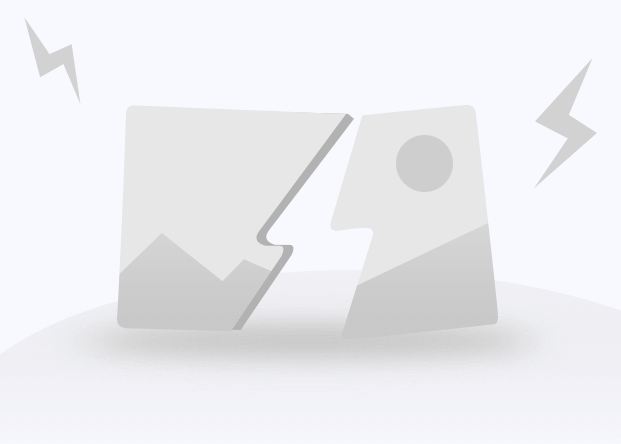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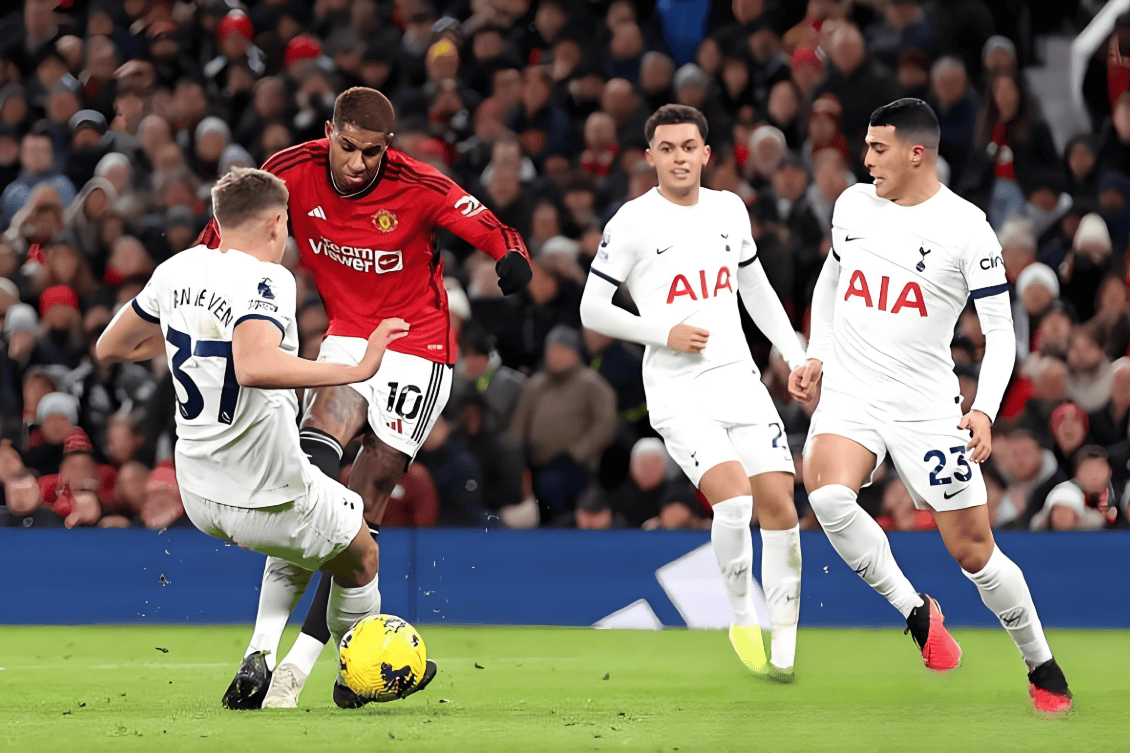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网友评论
最新评论